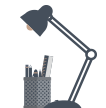「妳的縱膈腔有一顆十三公分的腫瘤。」闔家歡慶的除夕前一天,二十歲的我,被宣判成為一個病人。
回首過往,幼時母親離家、求學遭霸凌,家境貧困一度需以廚餘果腹,為了挑起家計一再放棄理想學校,即使人生路上苦難不斷,努力成為「普通人」的我,如今又被冠上「癌症病患」的美名,心中不斷問著:「為什麼是我?」
▼殘酷的現實,溫柔的人們
等待入院的短短五天,腫瘤就壓迫到脊椎神經,我從一拐一拐走路的瘸子,到下半身癱瘓,甚至無法自主排泄,那雙曾經帶著我東奔西跑的腿,不僅一動也不能動,還帶著隱隱麻痺感。看著自己狀況越來越糟,我才發覺原來活著是一件很困難的事。「胸(部)結締及軟組織惡性腫瘤」是診斷書賦予我體內腫瘤的名字,「癌友」成為我急於撇清卻無法撕下的標籤。看著因治療而日漸消瘦的身形以及副作用導致的落髮,原本就缺乏自信的我,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自我否定,我切斷了一切與外界的接觸和連結,只為保護連自己都無法接受的自己……。
逐漸習慣以醫院為家的生活後,我在網上看見與我年齡相仿女孩寫的抗癌文章,發現我們在同一間醫院進行治療,根據微小的線索找到了她的臉書,從此我的治療生涯開始有了變化。
女孩成為我結交的第一位戰友,讓我知道原來我並非孤身在世的年輕罹癌者。從那天起,陸續有其他夥伴加入,我們一起咒罵命運的不公、一起承受治療的不適、一起討論醫院的八卦,有哭有笑地推著化療機,走了一圈又一圈的病房,並肩尋找賦歸的航線。
▼歷經無數疼痛夜晚,只為拚一次活下去的機會
經過九次化療、三十次放療,腫瘤仍然沒有縮小反而有變大的傾向,原先化療藥也達到最高劑量,即使我恢復了行走能力,仍依舊無法迎向結束治療的那天。生活不容易,活著尤其困難,但我仍然深信只要好好活著,就是翻轉一切不幸的籌碼。縱使希望渺茫,只要有所冀盼,就要勇敢前行。
為了活下去的機會,我帶著病歷到各大醫學中心求診,評估轉院後進行了腫瘤切除手術,同時拿掉部分脊骨和肺葉,還背了整整三個月的固定脊椎背架。腫瘤消失了,但身上多了整整二十公分的傷口及兩條引流管,經歷無數疼痛難眠的夜晚,雖然難熬,但我還是撐過來了。屬於我的重生,正式展開。
▼我要為自己好好活一次!
回歸到所謂正常生活,才發現真正的挑戰才剛開始。
復學後,不敢拿下假髮、不敢向新朋友訴說罹癌經歷,治療所截斷的人生空白不知該從何填補。除此之外,定期追蹤也一再提醒我――死亡仍是生命中的重大威脅。進到身心科診間,我在醫師面前潸然淚下,原來這一切從未走遠,我仍然困在過去遭逢的所有苦難之中,包括罹癌。
從未體會何謂幸福的我,總是為了別人而活的我,想起初進病房時與自己的約定:「如果真的有未來,我要為了自己好好活一次!」
於是我拿下了假髮,以率性的極短髮示人,嘗試為自己建立新的身分;認真讀書,爭取獎學金;挑戰自己環島旅行;定期擔任志工,以微薄之力幫助流浪動物、偏鄉孩童、心智障礙孩童、無家者;因緣際會接受癌友團體的邀稿、訪談及分享;接受新聞媒體的影音專訪、上節目通告;開了「癌後餘生Momo」粉專,紀錄罹癌時的故事,以此鼓勵更多癌友。
▼用生命影響生命,一輩子的使命
好不容易大學畢業了,期間遭逢戰友們相繼復發、離世,殘存在我體內的癌細胞及不可逆的病理性骨折,都成為提醒我「把握當下」的訊號。我反覆問自己,有什麼是這輩子不做,就會後悔莫及的事?我申請了教育非營利組織「為台灣而教Teach for Taiwan」(TFT)的偏鄉教學計劃,以不到百分之十的錄取率成功選上計劃成員。離開自幼生長的台北,到屏東擔任偏鄉小學老師。我想以自身生命經驗,告訴那些可能正在經歷與我類似童年的孩子們:「人生不只是如此!」
年初,班上的孩子無預警的腦出血住院,她無法接受病態的自己。我告訴她我的故事,還傳了自己的光頭照給孩子看,她破涕而笑:「老師,妳光頭的時候好帥喔!」那一刻,我深刻的體會,用生命影響生命會是我一輩子的使命。
罹癌前,我看不見自己的價值,甚至懷疑自己是否值得被愛。直至今日,我才終於理解,原來與他人的歧異或是受過的傷,從不是汙點或是負面標籤,而是讓我們能判定自身獨特性的痕跡。